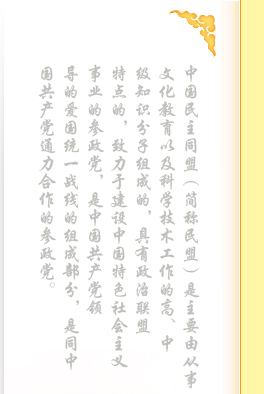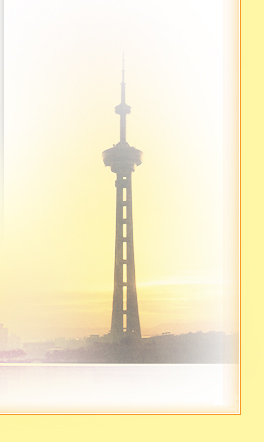记盟员潘敏钟 在我的朋友中,敏钟的机智、敏锐是出了名的,倘囿于篆刻一道而言,敏钟无疑是一个天份很高的印人。所以,早在十多年前,他便能在看似不经意间信手拈来的汉镜铭文――这一前贤浅尝辄止,却又契合其自身情性的艺术形式为己所用,所以,他能在治印伊始――这一多数篆刻爱好者们懵懂与躁动交织的“青春期”,便相继在中青展与全国展中获奖,得到了世人的认同。这固然是对敏钟既有成就的激励,但更是命运之神对敏钟走上篆刻这条寂寞之路的肯定。所谓“为艺之道,天七人三”,我以为用在敏钟身上再恰当不过的了。 敏钟醉心于治印,忽忽已逾十数载。我曾试图给他的印理出若干阶段,但由于敏钟初始对汉镜铭人印的把握,几近于顿悟,心念贯通遂脱手成“章”,因而他的印几乎无一不透射出一股神龙见首不见尾的玄机和堂奥,这也使得我对敏钟的印作分期的尝试几乎成为不可能,但作为当年曾与敏钟共同对镜铭文字有过偏爱之情的同好,回溯敏钟治印的历程,也还可以勉为其难地说几句。 敏钟治印伊始,有感于东汉铸镜匠师的天机流露,曾有意识地将汉镜铭文纳入印中,当然,为了使镜铭得以“印花”,必要的修饰包括对细微处的技术处理是必不可少的,总体印风属清逸一格,平淡简率,令人有耳目一新之感。收录于《第四届全国中青年书法篆刻展作品集》中的获奖印作,真实地记录了敏钟最初的探索。拟汉镜铭文入印,古已有之,赵之谦、黄士陵都可谓是开风气之先者,但敏钟却并未循前人亦步亦趋,但其早年撰述的《关于赵之谦汉镜铭文入印的探究》一文中,敏钟一针见血地指谪赵之谦拟刻汉镜铭印的弊病全在于“锐劲”不足,之所以“锐劲”不足,乃是由于“赵之谦拟刻镜铭印,用刀多以碎切法为主,这样刻出来的线条,往往细碎、支离,自然难以表现出汉镜文的‘锐劲’。”即如黄士陵拟刻的汉镜铭印作,敏钟亦以为尚未修得正果,具体而微在于黄对汉金文的恣肆宕荡、一任自然的天趣以及单字的点、线、面的配合尚存隔膜。有比较就会有鉴别,有鉴别才会有深邃的思考与审慎的取舍,由此可见,敏钟初始取法镜铭之印的成功,并不少偶然的。 大致在1993年以后,敏钟的印作悄然生发出了一些变化,仍以给我印象最深的“镜铭印”为例:印文笔画的穿插腾挪使印面益见空灵,印文线条极细、几如毫发而不显得单薄,在保持了一如既往的“锐劲”质感外又注入大量“隶变书”的因素,特别是个别文字中大回转曲线的表现手法,既盘活了全印的气氛,又透射出绵里藏针的一面,使人感受到张力之美,诚可谓动人心魄。不过,我一直都认为,敏钟在“第六届全国书法篆刻展”中获奖的“无以为言”为代表的那批印作,尚不足以反映他这一阶段变革的最高水准。此后,或许是因为耽于琐事,敏钟的篆刻创作经历了一段相当长的沉寂,但我们偶尔相晤,聊的最多的仍是刻印,敏钟也总是用他那惯常的最辛辣的谕讽方式,在谈笑风生间臧否古今印人的得失,话语或不免尖刻,但持论却大都入木三分,发人深省。每每至此,我都不免对他油然而生出几许敬畏。譬如,敏钟对时下某些成名印人过于注重外在形式的做法甚为不屑,他认为:所谓“创新”的本质,乃是能借鉴一套古代文字书法体系融入印章之中,从而自建堂庑,这也成为一个篆刻家是否能成为经得住历史考验得真正大师的标尺。由此来观照早些年颇受印人尊宠的来楚生,他的气息承吴昌硕那样的篆刻大师,就是因为来楚生没有将一套古法的文字体系入印…… 如此活泼激越的思想,如此勇于针砭时弊的锐气,毓之以如此妙到毫颠的印感,终于造就出敏钟近年来面世的一批极恣意烂漫与精微细腻于一体的印作,则无论如何不会使我感到惊诧。他的这一部分近作,其布局经营的精巧、用刀的狠辣爽利,包括一些细节如虚实相生的小点的运用等,相信篆刻界的同道早已不再陌生,无须我再置一辞。我想说的只有两点,姑且也可以称得上是观感,其一,在创作思想上,敏钟业已超然于黄牧甫以来对汉金文类印作近乎约定俗成的种种“规范”之上,他以自己的“镜铭印”赋予了汉金文类印作以更为恣情率性的艺术表现力,为调合汉金文类印作的朱、白文统一――这一羁困印坛多年的技法矛盾,作出了有益的探索。能做到这一点,凭的是胆气。其二,在印面文字的结体配篆上,敏钟勇于在向传统取法的基础上变法,将形态多变、载体丰富的“隶变书”经夸张变形等处理后,广博地纳入到印中,从而使其篆刻创作构筑于一个基础更广泛、前景更广阔的层面上。能做到这一点,凭的不仅是胆气。白石老人印论有云:“可贵者胆”,敏钟风华正茂,笃学善悟,又兼具胆魄,仅以此论,敏钟的可贵便不言而喻了。 深秋已至,天气渐渐寒起来,又到了可以吃火锅的时候。遥想1993年底与敏钟初识、在夫子庙吃狗肉火锅的情景,宛如眼前。时间过得真快! 民盟文化总支 邵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