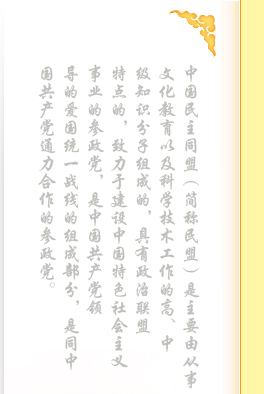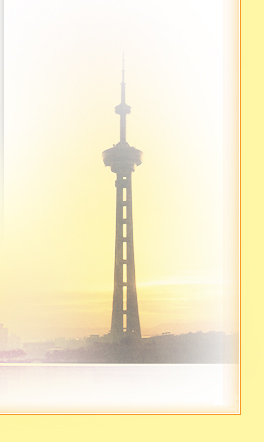.jpg)
春雨霏霏中,我有幸跟随民盟省市委领导前往贵州省调研教育发展情况,同时还有一项重要任务,就是看望已经从云南省曲靖市茨营中学转到贵州省毕节市威宁县支教的孙宁生老师。孙老师是南京师大附中退休教师,也是一名盟员。 8日中午,我们到达贵阳,下午用了近五个小时驱车二百多公里到达毕节市。在晚饭前,我们见到了孙宁生老师。孙老师面容清瘦,浓眉下的眼睛十分有神。省委吴主委、唐秘书长和市委戴主委与孙老师一同坐下,坐定交谈中才知道,毕节市知道我们来要看望孙老师,就由市政府出面,找到威宁县政府,由威宁县教育局安排吉普车将孙老师从学校接来,不到二百公里的路程花了七个半小时,足见黔道难行。 孙老师首先介绍了从云南转到贵州工作的情况。2011年初孙老师退休后即自愿到云南省曲靖市麒麟区茨营中学支教,两年后的2013年1月受田字格助学机构的邀请,担任贵州省毕节市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哈喇河乡田字格小学中营教学点的校长,为其工作一年,然后再回到云南去工作。这个教学点施教范围是回民区,共有140多名学生都是回族。村上原先是有学校的,后来被撤并了,现在由助学机构恢复兴办。但当地生活条件十分艰辛,甚至连手机信号都没有。学校刚建好,在通水通电前孙老师只能暂住在村民家中。为了尊重回民生活习俗,孙老师坚持清淡饮食。搬到学校住后,经常遇到停电,这时孙老师只能跑到村民家中,往炉膛里扔两个土豆,烤熟了当饭吃。来了一个月,已有四顿正餐未吃,身体日趋消瘦。 这个教学点共有8名教师,全是志愿者,除了孙老师以外都没有师范经历,且都非常年轻。但由于学校条件太差,有特岗教师分来,到学校后连行李都没有拿下车转身就离开了,也有志愿者坚持不了离开的。但孙老师年过六旬却坚持下来了,并且在交谈时语气和表情都显得十分乐观。 生活如此困难,孙老师却给我们详细介绍了西部农村学校“三元营养午餐”,就是每名学生每天有三元钱的午餐,由财政补贴,家长不要再负担。孙老师每个星期去一趟集市买菜,除蔬菜、米面外,也买一些牛肉,一次大约20斤,每天只能切4斤左右,每片只能切指甲盖大小。老师在食堂吃饭,每月也要交100元伙食费。那晚在饭桌上,孙老师说话不多,一直在忙着吃,但没有人感到这是失态或是不礼貌,相反都在劝说孙老师多吃些。 坐了一天的车,在崎岖山路上辗转颠簸,孙老师心里还是惦记着学校。听说第二天下午有捐书仪式,孙老师强烈要求提前到上午进行,仪式一结束就要赶回去。并且准备利用难得的进城并且有“专车”的机会,上街买一台二手电脑,带回学校用于日常管理,处理文字和图书管理,否则下次自己买了还要专门找人背上山去。 交谈中,孙老师多次提到了陶行知先生,说自己的行为较之陶夫子差距太大了,对大家献上的钦佩之辞显得异常的冷静。当问及工作和生活上有什么困难需要解决时,孙老师只说了教学点刚建好,学生年纪小又好动,没有活动器材,想要一些球拍、跳绳之类,这些要求在我们身边的学校里几乎都不能与“教学条件”一词相联系但在这个教学点却成为办学的困难和孩子们的“奢望”。
在与孙老师的交流中,许多人都谈到了自己,说能有时间像孙老师这样去支教也是不错的选择。其实,有些事讲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有些事看别人都觉得很难了,自己要想做到就更难了。 第二天,“天无三日晴”的贵州果然又下起了雨。我们一早去毕节市政府参加了座谈会,见到孙老师十分着急,原来是想早点回去,因为下雨的道路更加难走。赠完书送别孙老师,我坐在会场里想:孙老师要到下午五点才能到学校吧?在路上午饭吃什么呢?来贵州之前,我认真拜读了孙老师发在民盟市委网站上的“我的云贵支教生活”的“连载”,知道他自己要开荒种菜,就请我母亲买了几样蔬菜种子。但愿我从南京带来的种子能在威宁的土地上发芽、成长,也算是为孙老师的支教生活做点事情吧。 民盟南京市委农村教育烛光行动工作小组组长、教育工作专门委员会主任 张弛
|